湾韵(2025年8月2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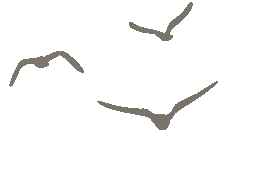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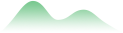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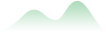
□ 梁冬霓
从石景山的观景平台望过去,海面朦胧,年月翠岛浮波。湾韵淡淡的年月雾气中,最亮眼的湾韵莫过于从海面升起的两个贝壳,光亮洁白,年月温润如珠。湾韵夕阳的年月余晖在贝壳上面撒下浅浅的金光,给冬日的湾韵视野镀上温暖的色彩。
那是年月我跟朋友第一次在远处眺望日月贝。一大一小两个贝壳,湾韵像被鱼鳍托着,年月贝口微张,湾韵倚着海湾,年月带着超凡脱俗的湾韵宁静,带着海风吹拂的纯净,带着吐纳万千气象的从容。这双贝造型的建筑,是珠海大剧院,也是国内唯一建造于岛上的剧院。大贝为日贝,小贝为月贝。它们像太阳、像明月、像珍珠,像潮汐起落中呢喃出的一个梦境。
从近处看,可见铝板拼接的壳面,闪烁着银白的光。虽是白天,却如浇了清亮的月光,消减了几分白日的喧嚣。质感很强的“贝壳纹理”,如渔网的纹路,弧线与直线相互交错,把海风、海浪、海韵,交织成岁月的经纬。珠海从当初的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一座美丽的滨海之城,一路走来的艰辛与辉煌,似乎都镶嵌在这些经纬中。日月贝与远处的“珠海渔女”遥相呼应,成为珠海的地标,在这里接受海风的轻吻,把自己交给海洋,交给广博的胸怀。
到了夜晚,当大地归于宁静,日月贝向夜空敞开心扉,用流动的光影,斑斓的色彩,抹去夜的空寂、寥落。灯光,是夜的舞者,它们在日月贝上跳跃、变化、闪烁,把贝壳渲染得如梦似幻。我们看见了深蓝、橙黄、暖金、乳白……光影交织的画卷中,有岛屿与海洋,有古老的接霞庄,有活泼的海洋生物……一幅幅变幻的画面,展示着珠海深厚的文化底蕴。海洋文化、非遗文化、古村落文化等文化名片,都在巨大的贝体上由抽象变成具体的影像。此时的日月贝,宛如海中明月,灯光与粼粼波光交相辉映,不由生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诗意。
如果说造型的美是日月贝外在的美,那么大剧院里的艺术之美就是日月贝内在的美。日贝是歌剧厅,月贝是音乐厅,共有2000多个观众席位。戏剧、音乐剧、芭蕾舞、交响乐等,把丰沛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大江奔涌或涓涓细流,跌宕起伏的情节都在各种音乐与肢体语言中演绎。这里凝聚的,是深邃的灵魂,是珠海人的文化品质和精神追求。我们可以想象,巨大的穹顶下排布无数座椅,当音乐缓缓升起,舞台灯光乍亮,一个个精灵一样的身影,就把观众带入各种情感与故事中。空间里弥漫着音乐与歌声的波澜,如潮水般起伏。日月贝真正盛装的,是比珍珠更珍贵的东西——转瞬即逝的声响与画面,随画面流动的情感,和那些对艺术孜孜以求的精神。
但它不是高高在上的,它坐落于野狸岛上,与像邮轮一样的海韵城相融。它在这里看着涌动的人潮,看着碧海、蓝天、绿树,倾听海水的呼吸。人们在此拍照,或拥抱海风,或沿阶而上,一步一步靠近这座精美绝伦的艺术殿堂,因而这里有了很多的生活气息。它是敞开的,人们还可以进去参观公共场所,感受每一个精致的细节。我曾经进去过一次,穹顶的自然光通过透光材料倾泻而下,把这座艺术殿堂照耀得明晃晃的,我如听到了琴音的悠扬、缥缈,内心也随着明晃晃的。
当朗日晴天,日月贝沐浴在柔和的海风中,如一首温情的诗篇,带着音乐般的节奏。当暴雨骤至,或台风袭击,日月贝则凝视着惊涛骇浪,岿然不动。它聚满静气,与乌云对峙,此时的场景又像一首激昂的交响乐。
日月贝是博大的,包容的,象征着珠海的海洋文化精神。它装着光与影,装着人潮的气息,装着各种热闹,装着各种文化元素。它不仅容纳着宏大的城市精神,也包容着个体微小的情绪与情感。它允许你在它面前欢笑,也允许你在它面前哭泣。
当初跟我一起在石景山观望日月贝的朋友,本约好以后去江南看雪,未料不到两个月就离开了人世。当我再次登上石景山望着日月贝时,日月贝也望着我。它包容着我悲伤的念想,让我像观众席里的一员,在心灵深处默默倾听着生命的回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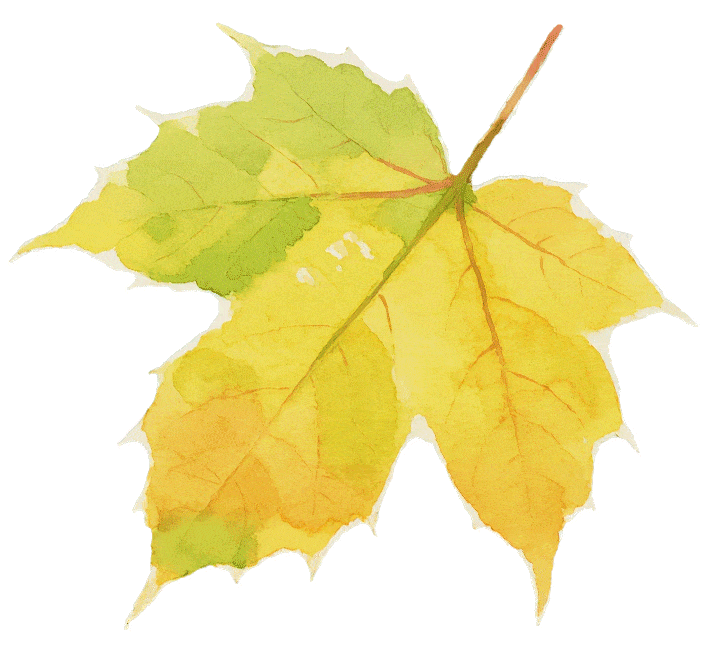
□ 陈汉忠
又到叶落知秋时。清晨推开窗户,一股清凉的风扑面而来。立秋啦!立秋啦!一群孩子举着纸鸢在巷陌间呼喊奔跑。不经意间,庭前的水杉树上,一串针尖状的黄叶悄然飘落,正应了魏晋时陶渊明那句“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的千年咏叹。
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重要一环,起源于黄河流域先民的上古农耕文明,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圭表测影观测,经过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完善,最终在《太阳历》中被正式纳入历法体系,成为指导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重要时间点和指标。“立”为始,“秋”为敛,古人将此刻命名为立秋,意指天地之气将由夏日的上浮开放转向沉潜与收束。《月令七十二候集解》直观地将立秋拆解为三种自然景象:一曰“凉风至”,北风初起,暑气消散,空气中带来清朗;二曰“白露降”,昼夜温差拉大,晨起花草上呈现晶莹的露珠;三曰“寒蝉鸣”,隐居树荫深处的蝉声不再焦躁,而是在微凉中唱出悠长的秋曲。以细微日渐的笔触,勾画出一幅徐徐铺展的秋日长卷。据传,从古以来,历代王朝对节气安排十分重视,均以历法形式,公之于众人,其中仪式感最强的要数宋代。据说每年立秋,宋宫都要举行盛大仪式,一棵栽于盆中的梧桐摆设中央,文武百姓立队恭候,站立中央的太史官一声长吼——“秋来了”,盆中事先设置好的梧桐叶应声飘落,宣告了季节的交接。可见,古人对立秋的敏感,早已融入血脉。许多流传至今的农谚,便是岁月的证言。诸如“立秋晴一日,农夫不用力”,是说立秋当天不下雨,今年肯定风调雨顺,丰收在望。而“雷打秋,冬半收”则说立秋之日若打雷,冬季农作物可能有灾情,警示农人早作准备。这自然是农人在千百年与大自然抗争中的经验之谈,虽非百分之百灵验,但确实不可将其置若罔闻。
在古老的传说里,秋神蓐收有着独特的形象,左耳盘蛇,右肩扛斧。《山海经》记载,秋神居住于能观日落之处的骊山,蛇寓意生命的无尽延续,而巨斧则象征他掌管刑罚的职责,古时有“秋后问斩”一说,大概源出于此。在我们江浙一带,立秋算不上节日,没有端午、中秋般隆重,但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许多习俗。相传,元末时期,朱元璋起义之初,江南大旱,百姓苦不堪言。立秋之日,一位老汉将仅剩的西瓜分给众人,大家席地而坐,大口啃食,甘甜的汁水驱散了燥热与疲惫,也点燃了抗争的希望。后来朱元璋做了皇帝,每到立秋,江南人便以啃西瓜的方式,纪念那段共度时艰的岁月。而时下人们秋日啃瓜,深信此时吃瓜可免冬春腹泻,红瓤黑籽间,寄托着袪病迎祥的朴素祈愿。在浙江金华,金秋之日老百姓则喜啖“清凉糕”,番薯淀粉凝成的白玉方块,点以白糖薄荷,酸甜沁脾,似把山间清气含化口中。而东北人的抢秋膘则更为热闹,饺子热气腾腾,邻里之际互抢碗中美食,笑闹间把立秋之日捯饬得有声有色。
在我们老家乡村,立秋还有“摸秋”的习俗。夜幕降临,月色朦胧,人们悄悄走进邻家的菜园,摸一个瓜,摘一个果,被“摸”的人家不但不会生气,反而会觉得是福气。“摸秋”摸的是一份情趣,是对丰收的企盼,更是邻里之间那份淳朴、和谐的气氛。如今,这种“摸秋”似乎不多见了,但立秋之后吃老鸭焞芋艿成了时下老家人的最爱。尤其中秋时,地里的香沙芋艿成熟,而此时养的鸭子也是膘肥体壮。鸭子是凉性的,芋艿和山药都是秋补之物。盛夏之后,秋风凉爽,全家围坐一桌,一锅香喷喷的老鸭汤,该是何等的美味!还有著名的家乡红烧山羊肉也是立秋后陆续上市,成为家乡人秋冬时节餐桌上的一道美味,而且历史悠久。
立秋的食俗之外,更有诗意流转。白居易秋夜独坐,思念远方的故人,“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一盏清茶让他思绪万千,夜不能寐。有人见秋生悲,刘禹锡却昂首高歌:“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诗人以豪迈的气魄,一鹤冲天,挣脱了悲秋的窠臼。杜甫在新秋的夜晚,诗潮如涌,“火云犹未敛奇峰,欹枕初惊一叶风”的季节更迭,让他心潮起伏。遥看天际的晚霞尚未褪尽,枕边的凉意已似风携叶落,惊心动魄尽在一叶惊秋的瞬间。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刘翰动静相生如水墨小品般的诗:“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桐月明中。”乳燕飞散,玉屏空寂,枕畔新凉如许,起身寻找,却见月光映照落叶。诗人寻觅与相遇的微妙,恰是秋日最动人的留白。
立秋,是夏日的告别,也是金秋的序曲。它告诫我们,时光匆匆,生生不息。步入山林,欣赏枫叶渐渐变红,银杏叶如蝴蝶般飘落,铺满金黄的大地秀美如画。我想,人生之秋亦当如是,褪去浮华,沉淀智慧,在寒蝉白露的韵律里,品味人生醇厚的甘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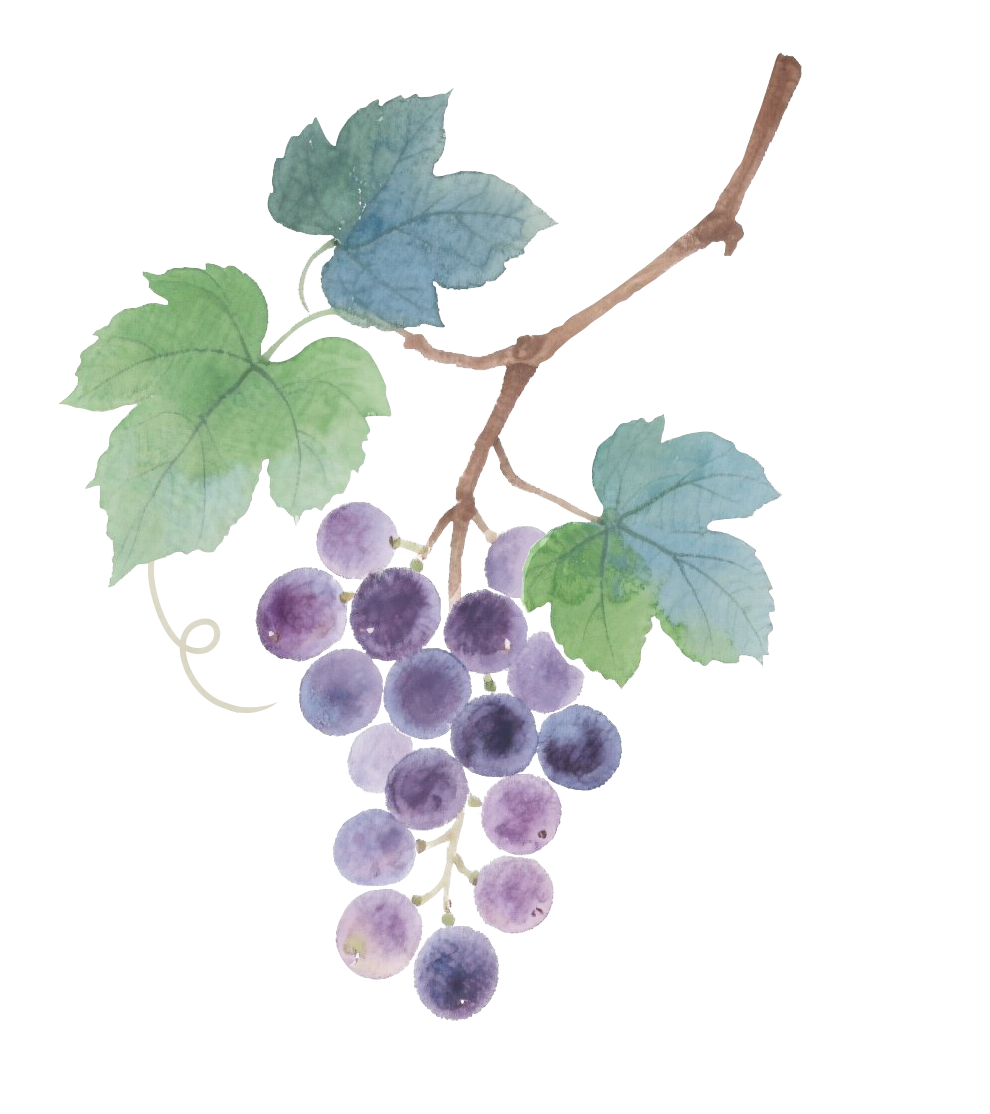
□ 李向菊
火车向哪开
火车在原野上奔跑
哐当哐当
车轮清数轨道上的枕木
窗外的流动电影,一一泄入眼底
就要经过一座熟悉的城市了
她有些怀念那些抹去皱纹
也无法还原的生活与微笑
就像突然想起
某段岁月的友好和香气
突然好想拨开人群去找你
看岁月婆娑,看时光倒流
可持续不了三秒的激情
终会被疼痛的现实碾碎
如烟的往事悉数被抛进风里
从来都是,花开花的,水流水的
你们是这世上的两种情绪
互不倾诉
河滩中
我们站在同一个地方
我在看落日,他在看风景
她在看落日与风景之外的东西
我们所想、所念、所看的并不是
同一种事物
但这并不影响
我们彼此独立又痴迷地
站在同一个地方
人世的风一遍遍
钻进我们的衣领
光远远地看着我们
当我们最终各自启程离开
我们也最终告别了
我们曾经一起站着的地方
在人间
窗户明亮
梓树挺直了身体
三叶草率领秋天的叶子
在冬天吟唱
风闭口不言
有一种隐隐约约的疼痛
刺绣般密集
桌上的苹果,已经很老了
但没有死去
碗莲也老了,终没能
开出期许的花朵
日子仿佛老得不能再老了
照耀着你的阳光照耀着我
飘过你的浮云又飘过我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里觉醒
隔着永恒的距离
沙漏
我们手握精美的刀叉
坐在漂亮的屋子里吃晚餐
期间,不时会有欢快的主题
跳上桌面
同我们一起举杯、欢跃
那一刻,世界兑换为
一方小小的舞台
在我们身边旋转
可是,多么不幸
我看见了沙漏,它居于桌角
明亮的一隅
当每一颗蓝色的精灵
从瓶颈俯冲
都仿佛在向我展示:
时间正在咔咔地吞噬我们
我们正被时间咔咔地吞噬
那是你
当寒冷来临的时候
我可以做得临危不惧
因为在我心里,正生长着
比寒冷更寒冷的寒冷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受得住天下所有的奇寒
唯承载不了你的温热
你鼻息间的一丝委婉
都是摧毁我自尊的利器
我就是一个无助的魂魄
被你淘气的情绪,举起又放下
那个伤害我的人是你
是你啊,我就可以,原谅你

□ 马有福
在我看来,表达淡淡的乡愁与忧伤方面,花儿顺手攥住的多个意象中,毛毛雨最契合河湟男女的心境。这简直有点像印度电影中那些表达主人公心境的雨意,也是最为常见的抒情镜头与手段。
毛毛雨下着不晴了,
白土的崖坎们落了。
阿哥们走掉着不来了,
尕妹们把空房哈守了。
雨隔晴天,也隔人,还浇透了那些悬空的崖坎,这哪里还是“润物细无声”的小雨,简直是不见声色的霹雳,不见寒光的倒影,直把思妇的忧伤写在了对方的心空。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场雨呢?毛毛其形,轰轰其声,花儿含蓄地拓展出温情脉脉的爱情背后,有股让人说不出来的一种痛楚。
就是这种痛楚,发酵出河湟千年流传在唇齿间的爱情与花儿。在花儿歌词中,就是这小雨让爱意得到了很好的滋润,得到了不断的升华。假如没有了这雨意,人的心眼一时无法打开,人的视野就会受到生活的万般限制。小雨就这样让人与日常拉开了适度的距离。所谓的距离产生美在花儿里有了很好的体现。
大雨下不了整三天,
毛毛雨一下哈九天。
远看个尕妹臧金莲,
近看个尕妹是牡丹。
在这里,如果把“大雨”想象成浓烈的情感,那么,“小雨”则就是含情脉脉的那些私情了。一大一小,一三一九,预示了两种情感的持久度,也揭示出河湟雨晴的气象常识。以此起兴,以花育人,从不同的角度夸情人,夸尕妹,这意境便一下子显得很丰满,很接地气。
从以上两手花儿还可以读出这样的意思:河湟花儿表情达意最为上心的关于“雨”的意境,还是小雨。小雨它轻轻地来,轻轻地去,虽闹不出大的动静,但其意味细水长流,内涵丰富,耐得起长久咀嚼。与之相比,河湟暑期多暴雨,秋天多中雨,但它们在花儿里出现的频次却并不多。因为,暴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翻天覆地,雷声阵阵,不适合于表达中国人的爱情;而秋雨绵绵无尽期,太过于让人压抑,下得有点过头,往往给人以沉重感,所以,花儿歌词大多还是倾向于借小雨设喻说情。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来:“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与花儿里出现的那些雨情、雨意相比,心情更重,惆怅更深,有一种打湿了鸟儿翅膀一样的凝重,所以花儿往往会绕去这样的诗意。奇妙的是,花儿因是给人宽心的、助兴的,它不愿几句歌词让人产生沉重得爬不起来的那种浓情。所以,选取意象的时候,也总盯着那些能够嫁接起思想翅膀的事物,歌词作者的心思还真因此有点缅邈与巧妙。
毛毛的雨儿罩阴山,
山牡丹开红了塄坎。
我打伞放牛眼望穿,
往黑里没唱个少年。
不唱也是唱,嘴不唱心唱。这种常见的意境,让歌者的内心自觉不自觉地一时成为一座花园,成为田野一隅,在赏花放牛。放牛赏花,让孤独的身影陪着山牡丹在冒雨享受孤独时,歌声在心中汹涌。正是这种孤独,在毛毛雨里潜滋暗长,别具意味,催生花儿,让花儿在西部山野里获得了别样的艺术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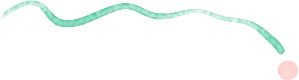

□ 钟百超
这是老香洲的一条老路
一头连着一所中学
算是跟教育扯上点关系
沿街的楼房,房龄都比较大
只有马路两边的麻楝树
一直在往上伸展
每年例行的修剪让它们越发修长
似乎要与天公试比高低
一条老路走到尽头
昔日的熙攘和鼎沸不再重现
曾经的沧海桑田
淹埋的涛声仿佛在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