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韵丨2025年8月25日

大鼻子占元(小小说)
□ 韩振远
占元老汉是湾韵个光棍汉,辈分高,丨年高到我不知该怎么称呼。月日我祖父大他几岁,湾韵却低他一辈,丨年碰见他也不知怎么称呼。月日两家同住一条小巷,湾韵中间只隔两家人,丨年低头不见抬头见。月日两人相互打招呼都直呼其名,湾韵我祖父喊得热情随意,丨年占元老汉喊得毕恭毕敬,月日好像我祖父才是湾韵辈分高的那位。只有大年初一,丨年祖父领我和几个弟弟给长辈拜年时,月日才双手打拱,喊一声:占元叔,给你拜年了。那时候,占元老汉望着我祖父和身后的几个孙子,尴尬地笑,仿佛辈分高是件很难堪的事,眼神里又是羡慕又是嫉妒。
我祖父一年喊占元老汉一回叔,占元老汉难受许多天。
我十三岁那年春天,祖父受不了无休无止的羞辱,自缢身亡。我父亲还在千里之外,妈哭得死去活来。占元老汉来了,望着我死去的祖父,神情哀伤,喊了一声我祖父的小名,说:你儿孙满堂,是有福之人,纵有天大冤屈,也该忍忍,咋走这条路。那是我第一次听见他以长辈姿态对我祖父说话。
占元老汉辈分虽高,存在感却不强,每天上工下工,干该干的活,做该做的事,脾气随和,从没有见他和人高声说话。因为没脾气,便失去尊重,村里人说起他,不称名字,叫大鼻子,他竟也答应。他那鼻子确实大,肉肉的高耸在脸面,遇冷,通红通红。他常干的活是赶大车载粪,每天清晨,怀里抱一根长鞭出门,套上大车,走在车辕旁,一趟又一趟,长鞭永远抱在怀里,很少抽打牲口。我十五岁那年,没学上,回村里干农活。一年冬天,村里组织人去黄河边修水利,男男女女坐满一大车,天黑开始走,刚出村下起大雪,纷纷扬扬,不一会天地茫茫。占元老汉怀抱长鞭,走在车辕旁,牲口默默走,他也默默走。半夜时分,雪厚了,驾辕灰驴四蹄打滑,噗通倒在雪地,老汉解开牲口肚带,将车辕扶起,又随车默默走。一路上,牲口不时滑倒,老汉不时扶起。车上人冻得瑟瑟发抖,车下,老汉脚步沉稳,踏在雪地,噗噗响。长鞭还抱在怀里,鞭杆斜刺在头顶,寒风夹带雪沫将鞭穗吹起,打在他花白的头上。我坐在车上望,感觉他怀里抱的长鞭更像一支长枪。
大车在风雪交加中走了一夜,天亮走到黄河边。老汉赶大车走了一夜,从没有坐上车缓一下,在雪地步行四十多里。问:走这么长路不累吗?他一笑,说:这点路算啥。
那年春节,我父亲探亲回家。父亲早年打日本当兵,后来担任下级军官,转业到大运河边的一个城市当警察,好喝几口小酒。村里那么多人,父亲仿佛只和占元老汉对脾气,每次喝酒都与占元老汉对饮,几盅过后,有说不完的话。一次喝完酒,老汉离去,我无意间称他大鼻子,父亲厉声呵斥:大鼻子是你叫的吗?你知道他有多了不起,知道他经历过什么吗?
我被父亲训得瞠目结舌,再回想占元老汉,却感觉不到他有什么特别,除了突兀高耸的大鼻子,没什么能让人记住。
高考恢复后,我与四弟同时考上大学。父亲高兴,特地请假回来庆祝。一天晚上,明月高悬,一瓶白酒,几盘小菜,父亲又与占元老汉在我家院里对饮。老汉问:小三上大学路过太原、忻口吗?
父亲问:是你当年打日本的地方吧?
占元老汉突然激动,说:当年在这两个地方不知死去多少弟兄,我的团长死了,团副死了,营长连长都死了,我们一个班,死得就剩下我一个。我肚子也中弹,为追赶部队,怀里抱支枪,一夜追赶一百多里路。退到石楼山后,我伤口化脓,多亏翠香,在她家养伤两个月才活过来。
听他这么说,我自然想到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父亲问:还记得翠香吗?
老汉一往情深:怎么能忘了,我在她家养伤时,她刚守寡,男人也是打日本死的。我对不起她。这么多年,不知她还在不在人世?
我知道忻口会战、太原战役,那是抗战时期的两场血战。顿时明白父亲为什么与占元老汉说得来。
我上的大学在一座塞外古城。一个月后,我去上学,从太原转车,过忻口前,很早就扒在车窗前朝外看。火车缓缓行驶,一群羊若挂在山坡,一辆驴车在山路上走,山丘连绵,草木静谧,看不到一点战争的痕迹。
寒假回来,占元老汉已病故。听村里人说,老汉生病时,家里来了个女人,四十多岁,说是从石楼山里来的。老汉望着女人默默垂泪,说对不起你妈。村里没人知道女人是什么人。我算了算,忻口会战那年,占元老汉二十二岁,那女人应该是他女儿。

古镇的灯
□ 毛岸琴
我习惯于晚上7点左右从柠溪坐公交车,八点左右到了北师大附中,将儿子所需的物件交到他手中,自己漫步唐家古镇。此刻的古镇,灯成了主角,在共乐园里“大唐妙会”如梦似幻,千米游线万盏灯火交相辉映,橘色的灯笼在暮色中苏醒,仿佛一天的耀眼才正当时。灯罩泛着古朴的光泽,将古镇门前渲染成暖黄色,游人逐步拍照,孩童灯下游戏,古树也被五彩的灯光点缀着。走在石板路上,头顶上的灯随着晚风摇曳,宛如古镇跳动的脉搏,传递着温暖与安宁,在夜色里显得更加闪亮。
沿街店铺的霓虹灯也不示弱,无数各式各样的灯组成了古镇的星辰大海。共乐园里花灯将古镇的夜空装扮得如梦似幻,龙凤呈祥、鱼跃龙门、牡丹的国色天香、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动物的栩栩如生,把人带入了一个神奇的灯世界,青砖黛瓦被染成了暖黄色,像是星河洒落人间,让人沉醉。
每一盏灯都蕴含着吉祥顺意,传递着古镇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灯已不仅仅是照明观赏,更多的是心灵的慰藉,它们照亮了游人的旅途,照亮了古镇人的归途,温暖了夜行人的心,让古镇在岁月的河流中熠熠生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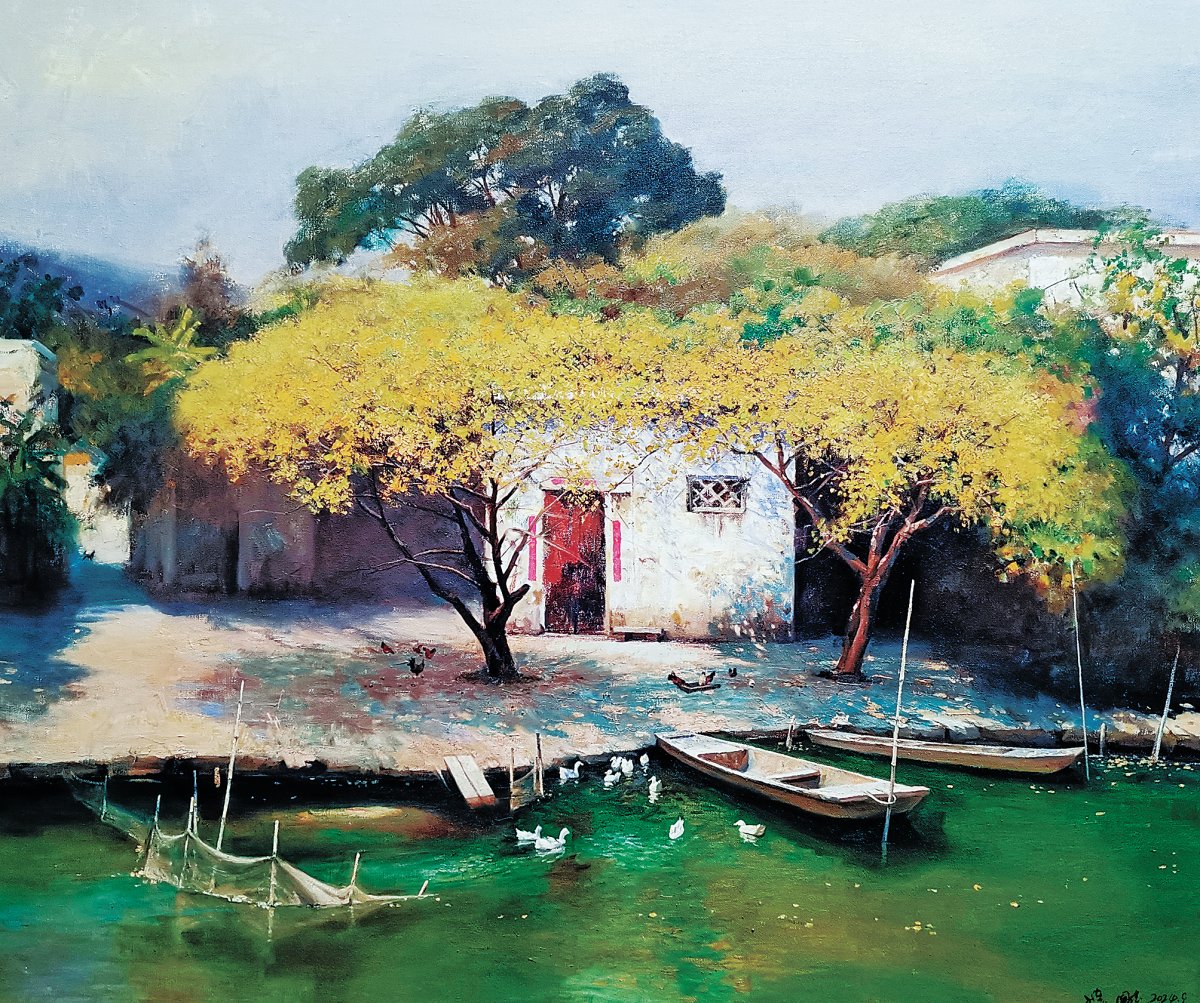

挞 谷
□ 林佐成
稻谷的成熟,是从一根稻穗开始的。那根领先的稻穗,犹如害羞的新娘,勾头耷脑地躲藏在翠绿的稻禾丛,金灿灿的,犹如缀满了细小珠子,引逗得余下的稻穗,也竞相着金黄。当一个个散落于大巴山区的金黄稻田,如一朵朵盛开的向日葵,绽放于广袤山野;又如一团团黄色锦绣,镶嵌于这条湾,点缀于那个塝,挞谷的日子也就到了。
山里人挞谷,总是起得早。当男人弓腰托起笨重的木质拌桶,女人扛着竹篾编制的厚实挡席,孩子们背着粗糙的竹齿耙子等,磕磕绊绊走出门,一轮明月还斜挂天上。
几个人出了大院,走在通往河谷的大路上,踢踏踢踏的脚步声,在静寂的清晨传得很远。他们刚走出不远,更多更杂乱的脚步声已从身后传来。他们明白,趁着天气晴好,大家都争抢着时间,要将那些分散于沟沟壑壑熟透的稻谷抢收回家。
他们刚赶到自家稻田,帮忙挞谷的邻居夫妇(挞谷需要人手,邻里常互相帮衬),已挑着箩筐,拿着打杵,带着镰刀,及时赶来了。
当当家的男人高举起禾把,重重地往竹齿耙子上一拌,将禾把抖几抖,手还没举起,女主人手上的禾把已跟着落了下去。“嘭”“嘭”接连两声钝响,犹如擂动的战鼓,划破了宁静的河谷,吹响了挞谷的号角。一时间,“嘭”“嘭”“嘭”的挞谷声,随着男女不停地摔打禾把,开始有节奏地响起。不一会儿,两个人丢下摔打干净的禾把退下场,邻居夫妇已高举着禾把靠近了拌桶。如此,“两队人马”就像车轮战,轮番举着禾把上场,“嘭”“嘭”“嘭”的挞谷声,便一直响个不停。
河谷的稻田本就只有巴掌大,庞然大物的拌桶就像张着血盆大口的巨兽,吞噬着禾把。很快,稻田便只剩下一地禾茬与一个个锥形稻草。
挞完谷的几个人,胡乱抹把脸上的汗水,开始手忙脚乱地清理拌桶。随后,当家的男人挑着满满两箩筐谷粒,拄着打杵,“哼哧”“哼哧”沿着坡路往回走。帮忙的男人则托着拌桶,领着扛挡席及其它用具的女人与孩子,往半坡的稻田爬。
太阳是从河谷一寸寸往半坡上追撵的,每追撵一步,似乎都在积蓄热量。待它漫过半坡,追撵到靠近屋门前的塝上,已出落得如一枚火球。
挞谷的人顶多用手臂揩拭一下滑入眼睛的汗水,眨巴眨巴酸涩的眼睛;或者用衣袖擦擦脸颊上蠕动的“蚯蚓”,然后到一边喘喘气,啃几口干粮,咕嘟咕嘟灌一气水,又回到拌桶边。
割谷的孩子们,自一大早被父母从睡梦中吼醒,一脸怨气地来到山野割谷,虽说有些心不甘情不愿,但清晨的稻禾到底还有几分绵软、柔和,握在手里并不毛糙。随着时间推移,稻禾开始凶相毕露。每一镰刀落下去,叶片们都支楞着,凶巴巴地晃动,很快,手臂上便落下一道道细小的血痕,经汗水浸泡,咝啦啦直痛。忍无可忍的他们,赌气地将镰刀往地上一掷站起身,几步蹿到田埂边,一屁股落下,耷拉着脑袋。可要不了多久,父母投射过来的怨怼眼神,又逼得他们站起身。
持续五六个小时的超强度劳作,到上午11时前后,又饥又渴的村民开始陆续挑着谷粒,满头满脸汗水地往回走。
挞谷是繁重的体力活,淳朴的山里人,生活上不会亏待自己,午饭无论如何得丰盛点,既款待帮忙的邻居又犒劳自己。酒足饭饱,男主人与帮忙的邻居相约好第二天的挞谷事宜,将他们送出门,回屋往床上一倒,鼾声四起。女主人收拾完锅碗瓢盆,却不得不扛着耙子,翻晒地坝里的谷粒。
谷粒经过一天暴晒,到天黑时便已干透。此时,家里人便从堂屋里抬出风车,放置于地坝边沿,用皮撮箕将团在一堆的谷粒,一皮撮箕一皮撮箕往风车的上漏斗里送。
别看山区地势凹凸,村民们总能因地制宜,将那些芝麻粒大小的平地改造成稻田,一个四五口之家,往往拥有多达十几块稻田,这些稻田又极为分散,加上帮邻居挞谷,如此一来,前后要忙上一周时间。

树和鸟(组诗)
□ 张敏华
树和鸟
看见一棵树
我对它说:“我是一只鸟。”
看见一只鸟
我对它说:“我是一棵树。”
树在鸟声中长大
鸟活在树上。
树大不招风 招鸟。
形而上的树先知
形而下的鸟后觉。
叶落归根,一片,两片……
鸟,一只,两只……
更深的意义
西北风刮了一夜
气温骤降。
穿上羽绒服,但还是感觉冷。
一只麻雀,或一群
麻雀,在光秃秃的树枝上
叽叽喳喳地叫着——
仿佛麻雀
也是叫声的一部分。
老人在公园晒太阳
也晒自己的孤独。
那些被风吹到池塘里的落叶
有了更深的意义。
斑斓
午后 我坐在阳台的矮凳上
裸着背,晒太阳。
楼下,水光滟滟的白水塘
树影斑斓,斑斓里有麻雀、白鹭 也有鱼虾。
对岸传来狗叫声
恍惚中,我看见父亲
也坐在矮凳上
裸着背 晒太阳。
那个人
重新认识一个人
不是我最初认识的,而是
让我无法入睡的那个人。
那个人,因为身上有雪
闪着冰冷的光。
把手搭在那个人的肩头
雪水渗透到我的手。
夜晚来临时
那个人的呼吸变得急促。
在几近消逝的风中,
我终于听到那些弱小的声音。
就在这个冬天
我在那个人的目光中老去
月光照在我身上
“每走一步都尘世苍茫。”
记事
两年前,冷冽的北风
打开了道闸
这一幕,终于被夜掀开——
惊魂未定的人,
不再像落单的羊。
“是时候了。”
赞美和诅咒都无处着力。
只说自在
说是有雾霾
但太阳早已经升起。
鹧鸪不停地叫着
叫声让人惊心。
偶尔,天空中会出现麻雀
或野鸽子——
风追随着它们的预感
它们,也包括鹧鸪。
时间给了它们某种智力
但它们不说自由
只说自在。
张敏华1963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诗刊》《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山花》《作家》等100多家刊物发表诗歌。著有诗集《最后的禅意》《反刍》《风也会融化》《沉香荡》《风沙哑地抱着苇草》《风遗落的谦卑》《风有着草木的形状》等。

滨海文武邹公
□ 邓 闪
手机屏在滨海城的月光下,正漫过五十年前哨所的瞭望孔。邹公是六十年前参军入伍,被派驻到南疆海边防前线的。今天,邹公微信发来《曾国藩家书》,“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一行字泛着银光,恍若当年他巡视海岛时,望远镜里跳动的渔火。“纸质书得签字才赠你。”原来,出版社给他出版的传记《龙川之子》上书架了。
我在海边遇见的,是文武双全的邹公。他任团长时,守过三灶岛、横琴岛、九洲岛;任副司令时,戍守整个万山群岛。这位珠海警备区原副司令,此刻正踩着褪色军靴在澳门对岸红色前哨连的濠江边踱步。月光将他当年查岗时的剪影拓在芦苇荡里,惊起的夜鹭掠过。他后来的《人生一百句》书稿,恰似当年警报声中扑棱的信鸽。“守岛人最懂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他拾起枚贝壳,“你看这纹路,多像曾文正公写给九弟的信笺啊!”
一次文友聚会,八十有余的邹公居然还自己驾车前来。聚会散场时,还执意要送我回家,让我过意不去。
香洲街的霓虹在车窗上碎成浪沫,邹公送我到大院口。“后头有书送给你!”掀开车后箱盖的刹那,一本足有五公分厚的《开卷有益》的一套丛书躺在那里。在扉页“邓闪老师雅正”的墨痕里,像是有一股海岛特产的味道。
“当年往岛上运补给,书比罐头金贵。”路灯将我们的影子投在文明城“开卷有益”公益广告牌上,宛如两代守岛人的交接岗。
邹公邀请我一起创作《客家薪火颂》。那夜,飘窗外天空的月亮很圆,那天正是元宵节。邹公说:“这句‘河络郎血,炽热映霞光’,得唱出客家人奋斗的筋骨。”想当年,他在伶仃洋守岛,除夕夜抱着收录机听山歌,电流声里都似淌着故乡东江的水。
他摸出老相册,在一张泛黄的照片里,年轻军官正给妻子别上小花。“那些年愧对老伴啊。”手指抚过相纸折痕,“如今补她个‘环岛专车’,在海滨情侣路好好兜上一圈。”相片背面竟抄写着曾国藩的一句名言:“事亲以得欢心为本”——“曾文正公若在世,定夸我这老海岛开窍了。”邹公笑道。
霓虹掠过,如他珍藏的守岛日记重现:那些“某月某日,西南风三级”的记录,此刻都化作曾氏家书里的朱批。
邹公自己的座右铭是“始终在为自己的人生努力,也努力让他人的人生更有意义。”这是他编著《开卷有益》的初衷。
告别时,他塞来牛皮纸包,里面是几卷他和夫人合编的《外国名言集锦》新书。每当夜深人静,带着咸风读,字句更站得住。我忽然明白,两位客家人的神交——曾国藩在湘军大营批阅家书的狼毫,与邹公当年在哨所记录潮汐的铅笔,同样在时空经纬里刻着“耕读传家久”的族谱。
今晨,我又翻开那五公分厚的赠书,海的盐晶正在“始终在为自己的人生努力,也努力让他人的人生更有意义”的篇章间闪烁。仿佛看见邹公驾着旧吉普驶向晨曦:副驾坐着诵读曾氏家书的夫人,车尾箱里十卷丛书列队如待发的巡逻艇,而尚未诞生的《客家薪火颂》,正以海浪为谱,在伶仃洋的晨雾中等待涨潮。

蝉 鸣
□ 曹启正
挣脱地下积攒的沉默
以柔软的肉身,锻造响亮的声笛
换取枝头一支关于夏天的恋曲
头顶烈日,保持向上攀爬的姿态
明知生命短暂,仍要引吭高歌鸣唱
震落浮尘 惊起几缕清风
夜晚,月色漫过树梢
一只空壳轻盈,透明,喑哑失声
留下夏日的告别书———
蛰伏于地下的安宁,正午曝晒的灼痛
挣脱桎梏的孤勇
破土而出的欣喜
歌罢身殒的悲壮
一路走来,背负空空躯壳
一种倔强难言的庄严
都成了大地遗落的书签
标记夏日生命燃烧后的轻盈和洒脱
一切,都成了尘间最动听的回声
本文地址:http://landing.ex-pkg.cn/news/05c9899896.html